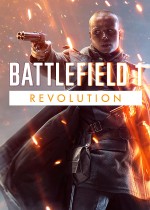E3 2016:这些残酷战役 将出现在EA的《战地1》中
1909年,劳伦斯凭借优异的成绩从牛津大学历史系毕业,随后立刻前往叙利亚参与对当地遗址的考古挖掘。但他来到当地之后,不久便发现,自己对当地人的兴趣远远大于考古本身。晚上,他经常在营地的篝火旁和工人们待在一起,从小道消息一直聊到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结构,这些都给劳伦斯带来了丰富的认识和经验。
1915年,劳伦斯被英军征召,成为驻扎在开罗的一名参谋军官。在他的同僚眼中,阿拉伯人毫无组织和纪律性,是一群乌合之众,但劳伦斯并不赞同这种看法,他认为,阿拉伯人是天生的游击队员,唯一需要的只是一位强有力的领袖——这位领袖将刺激他们、威胁他们,进而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战斗——1916年10月23日,劳伦斯确定找到了这个“给起义带来荣光的人”,这个人就是侯赛因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亲王。
在劳伦斯和英国政府考虑的候选人中,费萨尔不是唯一的人选,也不是最有竞争力的一个。但和父亲、众多兄弟和其它军阀不同,费萨尔脑海中始终存在一个宏伟的想法:这就是将纷争中的部落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进而将土耳其人彻底赶出中东。在劳伦斯的呼吁下,英国人为费萨尔送来了枪支、火炮和弹药,而作为实现这个设想的第一步,劳伦斯和费萨尔开始向北方重镇——亚喀巴前进。

费萨尔亲王(前方着长袍者),他后来短暂地成为叙利亚国王,但迅速被法国人驱逐
在沿途,他们忍受经着热风和沙尘暴的折磨,以粗面包和倒毙的骆驼为食。一路上劳伦斯穿着一身长袍,向各个部落兜售着“阿拉伯国家”的理想,这让费萨尔最终建立了一支上万人的部队。经过长途跋涉,亚喀巴的轮廓在地平线上清晰可见,但土耳其方面也开始调集援军,一场恶战似乎无法避免。然而,发生在城外的战斗却成了一战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500多名土耳其正规军被350名骑骆驼的部落战士击败,他们中有近400人被俘,其余则向北狼狈逃窜。

艺术画:劳伦斯和部落战士攻占亚喀巴郊外的土耳其军队阵地,他发动的这次袭击,不仅击败了数量占优的当地驻军,还令阿拉伯人获得了一个优良港口
随着亚喀巴的占领,劳伦斯打开了通往叙利亚的大门,费萨尔的梦想离实现也只有一步之遥,但就在此时,英国和法国却抛弃了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承诺,私下计划着对中东地区进行瓜分和占领。劳伦斯对这些一无所知,他依旧和部落战士们并肩行动,此时的土耳其军队士气低落,只是因为一条补给线,他们才能垂死挣扎——这条补给线就是汉志铁路。
作为当时中东地区为数不多的现代化铁路,汉志铁路于1900年开始兴建,从大马士革一直延伸到麦地那,其建造目的名义上是为了方便穆斯林去麦加朝觐,但其军事意义要远比宗教意义更为深远:通过这条铁路,土耳其人可以将军队部署到中东各地,但其绵延超过了1000公里,这使它变得极易遭到攻击。
这也是本节开头的一幕,它也在《战地1》的预告片中出现:在叙利亚附近的荒原上,劳伦斯耐心等待着地平线上的黑烟,只是,在现实中,他们并不会挥舞着马刀发起冲击——此时的他们装备精良,拥有机枪和TNT炸药。从1917年9月到1918年初,他们在叙利亚大举行动,平均每周都有一列土耳其列车被摧毁,正如劳伦斯本人的描述:“一声骇人的巨响,铁路从眼前消失,紧接着喷出一阵黑色的尘土和烟柱,足有60米高,60米宽。”与之一道支离破碎的,还有土耳其在中东超过500年的经营和努力——1918年10月,劳伦斯和费萨尔并肩作为胜利者进入了大马士革。
同一个月,奥斯曼帝国签署了停战协定。然而,此时,劳伦斯的事业却接连遭到打击: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公布了先前列强瓜分中东的秘密协定。劳伦斯得知此事,感到自己被政治家们出卖了,并为把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引错了方向而倍感后悔。
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劳伦斯与费萨尔一道前往巴黎,为争取阿拉伯国家独立做最后的努力,但他这些努力的结果都是徒劳无功。在巴黎和会之后,法国控制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控制了巴勒斯坦和伊拉克,这实际是对先前所有许诺的背叛。从那以后,阿拉伯人彻底放弃了对“国际公理”的相信,所有的期待也被转化成了仇视。这种态度被一代代的统治者们继承和操纵,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
对身在一线的执行者——劳伦斯,他无疑曾试图抵制这一幕,但在国际博弈这个“大棋局”面前,他的努力将注定毫无用处;而对幕后操纵的政治家们来说,他们从开始便抛弃了“公理”和“正义”,所有的行动只是为了一个目标——置对手于死地;高尚的口号更只是一个幌子,它吸引人们无条件地为它而战,劳伦斯和他的部落战士是如此,《战地1》封面的黑人士兵也是如此。
如果对1918年的局势做一个概述,它可以概括为:这场战争在摧毁帝国,也在走向结束。此时,俄罗斯已退出了战争,土耳其奄奄一息,奥匈帝国在内外交困中苦苦挣扎,德意志、不列颠和法国则在拉锯战中精疲力尽。这时,美国人走了进来,仅在1917年,他们就将80万名士兵派往了欧洲,同时抵达的还有惊人的装备和物资——而这些,正在影响战争成败的天平本身。

《战地1》的一个扩展包即以美军第369步兵团——“哈勒姆的地狱战士”为名
在开赴前线的美军部队当中,有一支特殊的战斗力量——陆军第369步兵团,这个团的成员是来自纽约的黑人——他们后来被称为“哈勒姆的地狱战士”。该团由威廉·海沃德上校在1916年组建。按照当时的法律,其从成立伊始便遵守着种族隔离制度,其普通士兵全部是黑人,而白人则担任军官。即使如此,非议仍然此起彼伏,有人认为,将黑人招募为士兵是一种浪费。但海沃德对此不以为然,他说:“我不认为士兵天生存在优劣之别。”
1917年12月,第369团在法国登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不是炮火纷飞的前线,而是风景如画的卢瓦尔河河口,在当地,他们修建道路、铺设铁轨、从港口装卸物资——这些“任务”其实更像是一种侮辱。军方当时的命令是:鉴于黑人在“智力上存在严重不足”,因此不能作为正规部队投入战斗——这激起了该团的集体反对,作为结果,1918年3月,第369步兵团被调往香槟地区,在法军的指挥下投入了作战。

美军第369步兵团成员在乘船前往法国期间的照片,他们最初没有承担战斗任务
这种安排背后的原因非常简单:经过四年战争,法国的兵员已经山穷水尽。不仅如此,由于当时法军从殖民地招募了大量黑人,因此其军队对黑人的歧视更少,指挥也更为得心应手。此时,战争恰好进入了一个微妙的阶段:随着俄罗斯退出战争,德国将部队从东线调往西线,以取得一次“决定性胜利”。
在这样的局面下,第369步兵团被部署到了阿戈纳森林,按照传说,这里曾是邪恶巫师的藏身之所,但在一战期间,它留给交战方士兵的印象并不是恐怖,而是难以形容的艰苦。在整个夏天,阿戈纳森林几乎都在下雨,粘土路变得泥泞难行,车辆滑进沟渠,马匹摔倒,让每个士兵精疲力竭。此外就是持续不断的炮击和冷枪——它们每天都要夺走许多人的生命。
作为黑奴的后代,第369团似乎天生就拥有某种超常的适应能力:他们学会了忍耐,并且将阵地视为荣誉和生命,为更好地同德国人作战,他们装备了大量12毫米短管猎枪——它们在堑壕中威力巨大,让德国人甚至宣称其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但协约国对这些抗议置之不理。
1918年9月25日,第369步兵团奉命向德军发动进攻,这场进攻是协约国阿戈纳森林攻势的一部分,在这一天,上万名士兵冲出积水的堑壕,跨过了因炮击和暴雨而无法辨认的战线。第369步兵团的目标是一座名叫Séchault的村庄,敌人的交叉火力最初令他们寸步难行,不断有人阵亡和负伤。但在愤怒的驱使下,这些士兵还是潮水般地向德国人的阵地前进。大规模的肉搏战开始了,尽管这些黑人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但他们依然勇敢地用左轮手枪、手榴弹、最后用刺刀进行进攻。黑人士兵亨利·约翰逊和约瑟·罗伯茨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在弹药耗尽的情况下仍然击退了一支24人的德军巡逻队,其中约翰逊在肉搏战中用短刀砍死了至少4名德军,其它德国人则狼狈逃窜。当进攻结束的时候,第369团已经挺近了14千米,将友军部队抛在了身后,前面提到的、两名士兵都被授予了荣誉勋章,它也是当时美军的最高荣誉。
1918年,团长海沃德在一封家信中写道:“这些士兵是我见过的最意志坚定的男人……他们不仅占领了大片的土地,还给那些怀疑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人们将他们称为‘哈勒姆的地狱战士’。”1919年2月17日,这些士兵从欧洲归来,在纽约第五大道进行了凯旋仪式,但光荣并非没有代价:1500名该团的士兵被永远埋葬在了欧洲大陆,幸存者则迟迟无法拥有和白人士兵一样的退伍待遇。不仅如此,美军中的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对黑人士兵的歧视,直到二战结束还没有消散,虽然黑人组成的第369步兵团从没有丢失一处阵地,但离收获真正的尊重和荣誉,他们只是迈出了漫长道路上的第一步。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来回顾下《战地1》的最新宣传片:
更多相关资讯请关注:战地1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