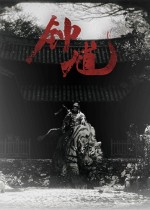《黑神话钟馗》钟馗历代形象变迁介绍 钟馗是什么神
第3页:从“侈谈神怪”到“人生世态”
展开如前文所述,钟馗与傩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傩仪式微下的形势下,即使老前辈“方相氏”尚难自保,钟馗在此浪潮中则未被淹没,而是走向了世俗化的新道路。正如前文所述,唐代的宫廷傩仪其严肃性和神秘性消散,转变为了娱乐属性,而作为除夕傩仪主角的钟馗尽管仪式也是遵守惯例。 但众多人扮成钟馗,浩浩荡荡,一定程度上已带有表演和娱乐的性质,再加钟馗并未“执戈扬盾”,庄重严肃的气氛显然淡化了。宋代以后,钟馗信仰也发生了重要转变,其特点是逐渐向着世俗化和民俗化方向发展。在敦煌写本《太上洞渊神咒经》中那个曾经与孔子、武王这两个文武二神并列作为统领捉杀诸鬼之神的钟馗,逐渐转变为辟邪驱祟的道具和象征,融入例行的送旧迎新的年节民俗事项之中。这种转变,从实质上说来,意味着钟馗信仰的神圣性逐渐减弱或消失,世俗性逐渐加强。而在明清小说中这一转变更为明显。明代所撰的《唐钟馗全传》该书更像是作者对于前代钟馗传说的归纳总编,在情节处理上 , 大体依傍前人材料,没能自出机抒, 只是简单的加工、拼凑、连缀、成篇。书中的钟馗从出身到降妖,几乎是毫无波澜,遇鬼杀鬼,全无意外,只是机械着做着搜世、捉鬼的反复循环,因此 , 小说只 能停留在记异述怪诞的“志怪”阶段。但到了清代《斩鬼传》与《平鬼传》则不同,两书中将钟馗塑造成了一个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壮士,运用大量篇幅书写钟馗自尽的情节;其中皇帝的昏聩、奸臣的谄媚、宰相的劝告以及钟馗的悲愤跃然纸上,而《斩》传为钟馗安排的两位副手——咸渊(谐音含冤)和富曲(谐音负屈)亦在二鬼身世中表现出无尽的对有才之士,却无立椎之地的悲凉。作者在有意无意之间以钟馗的故事描绘了中国封建社会下底层学子的真实写照;而两书中的鬼怪,也不再是《全传》中简单的反派炮灰,而是阳世众生恶欲的具象:
大凡人鬼之分,只在方寸间。方寸正,鬼可为神。方寸不正,人即为鬼。 世上何尝有鬼?妖魔皆从心生。
书目中的鬼怪名分如诌鬼、假鬼、奸鬼、捣大鬼、冒失鬼、龌龊鬼、温尸鬼、不通鬼、诓骗鬼、急赖鬼、心病鬼、醉死鬼、抠掐鬼等等,都难看出其精怪身份,更多反映着对世态炎凉、人心向背的讥讽。
从中可以发现,三本钟馗小说中,完成了从神魔志怪到讽世劝时的转变。更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发现钟馗“从神变得像人了”。宋代,钟馗从威严的傩仪之上,下降民间成为家家户户民俗祈福的对象,他们原先食鬼的血腥凶狠转为了驱邪避灾的简单化功能,明清小说中他从一个机械的、听天由命的捉鬼机器变成了在两传中会为了悲愤不公而以死抗争,面对鬼怪挫折会有气愤,有反思,有运筹帷幄,有奋勇向前的斩鬼神君。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此时的钟馗的形象也真正走向了人间,他凭借着民众的期望和想象,成为守护私宅家园的小神,能为小说中为反映着世态炎凉。他在市民笔下有喜有悲、有滑稽玩笑、有伏魔正义。也算这才是钟馗至今流传的原因,古今的钟馗是人民所希望、人民所需要的钟馗。
当然,也由于世俗化的影响,钟馗凭借着百姓寄托能够是正义化身,同样为了娱乐需要也可以是邪恶反派。明代的《太乙仙夜断桃符记》中,钟馗的形象是一个与桃符鬼同流合污,不但不降魔驱鬼,反而知情不报,令鬼怪长居主人家中的丑恶形象。《狮子赚》中钟馗更是被作者写成了一个贪赃受贿的奸邪........
更多相关内容请关注:黑神话:钟馗专区
责任编辑:铁板里脊歼灭者
- 第1页:起源
- 第2页:从驱鬼消疾大傩神到终南进士正神将
- 第3页:从“侈谈神怪”到“人生世态”
- 第4页:治鬼 镇宅 赐福 判子
- 第5页:东亚地区的钟馗
- 《逃离塔科夫》官方中文版下载
- 《深入矩阵》官方中文版下载
- 《GIGASWORD》官方中文版下载
- 《The Salesman》官方正版下载
- 《The Sushi House》官方中文版下载
- 《亡魂战纪》官方中文版下载
- 《Duck Paradox》官方中文版下载
- 《Pinball Spire》官方中文版下载
-
 1米6男和2米1女的坚定感情 寻5000被下药总裁的囧图
1米6男和2米1女的坚定感情 寻5000被下药总裁的囧图
 《漫威死侍》IGN8分!超英佳作 死侍台词幽默有趣
《漫威死侍》IGN8分!超英佳作 死侍台词幽默有趣
-
 《寂静岭f》加藤小夏提名TGA!本人回应:阿里嘎多
《寂静岭f》加藤小夏提名TGA!本人回应:阿里嘎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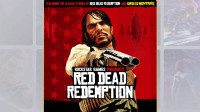 11月PS+游戏今日入库!《大镖客》需等到12月2日
11月PS+游戏今日入库!《大镖客》需等到12月2日
-
 《寂静岭》全新作发售日疑似曝光!紧随《生化9》
《寂静岭》全新作发售日疑似曝光!紧随《生化9》
 国产大作《湮灭之潮》新内容预热:Xbox发布会亮相
国产大作《湮灭之潮》新内容预热:Xbox发布会亮相
- 邓紫棋谈自己是S15"唯一中国人":进休息室立马就哭
- TGA 2025年度游戏提名公布!《光与影》等6款游戏
- 迪士尼终于醒了!宣布退出DEI 相关术语全部删除
- 向佑在美国遭歧视被往头上吐痰 哥哥向佐打断对方的手
- TGA提名明日公布:6款游戏争夺年度最佳!
- TGA2025提名完整名单:来看看你心仪的游戏有无提名
- S9冠军FPX告别《英雄联盟》!LPL官方回购席位
- 《明末:渊虚之羽》新版本周三公布!新服装要来了?
- 疑似唐尼复联5造型曝光!满脸伤疤、几近毁容
- 《塞尔达传说》首批剧照!林克塞尔达造型大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