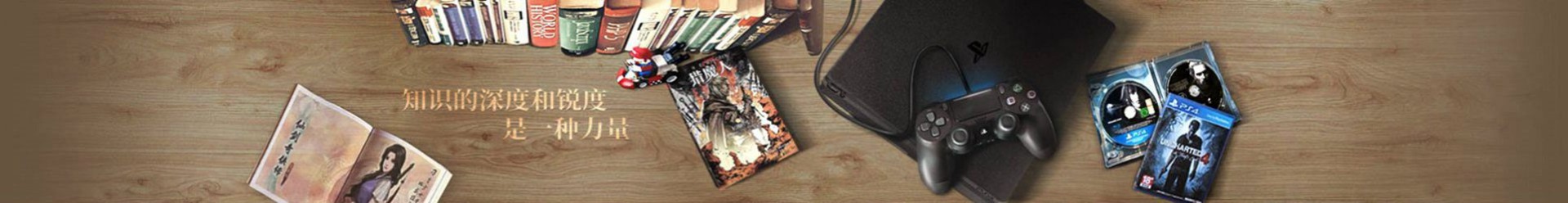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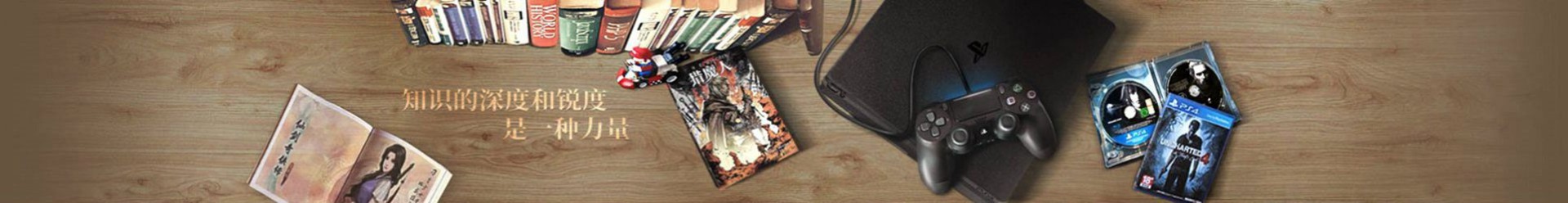
版权纠纷一直是美漫从业者的心病,与日漫“独立画家”的模式有所不同,美漫的版权往往直接归属于漫画公司。漫画家精心创作的漫画角色在专业的流水线工作室中被包装为品牌IP,为漫画公司源源不断地创造价值与收益。而漫画家们往往因为有约在先,只能拿到公司发放的基本薪酬。对此,飞扬跋扈的阿兰·摩尔早有不满。
尽管《守望者》在当时由DC漫画发行,但是作品自身拥有独立的故事与世界观,登场角色也皆为原创(创作过程虽然参考了DC漫画中的数名角色,但版权并无交集)。于是,当阿兰·摩尔与其好友戴夫·吉布森(《守望者》的画师)共同完成了这部引以为豪的作品,他们希望能以个人名义拥有《守望者》的版权。此时,DC方面表示予以支持,他们为此编订了一份合约,其中注明:只要《守望者》平装本在一年(任意一年)之内不会再版印刷,版权就将自动还归阿兰·摩尔与戴夫·吉布森。这看起来似乎是比不错的交易,DC方“出乎意料”的友好态度也让摩尔打消了顾虑。
然而,漫画家的算盘自然精明不过商人,《守望者》漫画取得的巨大成功让“不会再版印刷”的那一年迟迟无法到来,阿兰·摩尔翘首以待的《守望者》版权便成为了空头支票。摩尔远远低估了漫画读者对《守望者》的追捧程度,甚至在《守望者》签约完成之后还将其另一部著作——《V字仇杀队》的版权问题如法炮制。将其两部代表漫画作品的版权拱手让给了DC。
眼看着《守望者》接连不断地再版印刷,周边产品的分红却分毫不见,后知后觉的阿兰·摩尔这才如梦初醒,他终于意识到,DC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返还漫画版权。摩尔恼羞成怒,但也无可奈何,而随后的“DC漫画分级制度”更是让摩尔对DC失望透顶。尽管当初反对“分级制度”的漫画家不在少数,可唯有阿兰·摩尔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DC搞分级制度,我就立马走人。后来,摩尔兑现了他的承诺,正像《守望者》中的罗夏一样,当所有人都习惯了接受现状,委曲求全,阿兰·摩尔的决定依然是“永不妥协”。
离开DC漫画之后,阿兰·摩尔辗转于几家独立漫画公司,最终在韩裔漫画家吉姆·李的Wildstorm旗下拥有了自己的Imprint(欧美出版业中的特殊版权信息),然而就在签约后不久,吉姆李将Wildstorm卖给了DC,阿兰·摩尔的Imprint也成为了DC的囊中之物。虽然DC承诺绝不干涉摩尔等人的的创作自由,但其日后对Wildstorm出版物的某些“限制要求”还是被阿兰·摩尔视为针对自己的压迫与剥削。这让摩尔铁了心地要和DC划分界限,Wildstorm在职期间,阿兰·摩尔亲手终结了自己参与创作的“ABC宇宙”,没有再给DC留下任何“遗产”。

Wildstorm是Image旗下的分公司,Image最初正是由一群不堪版权压榨的漫画家共同建立,然而如今的它也成为了同DC和漫威一样的“老江湖”
2009年,由扎克施耐德执导的电影版《守望者》上映,影片对于漫画原著“近乎疯狂”的还原与致敬令一部分漫画粉丝大呼过瘾。然而对于那些抱着去看“科幻大片”的普通电影观众来说,院线版混乱、黑暗的色调与混乱的叙事令他们完全摸不着头脑。电影上映之初,影片的评价两极分化严重。《守望者》院线版为2小时40分钟,之后推出了3个小时的导演剪辑版,而直到3个半小时的“终极剪辑版”发售,电影版《守望者》在很多电影观众眼中奇迹般地完成了从“烂片”到“神作”的蜕变。当然,即便如此,扎克施耐德特立独行的“黑暗风格”与“影片对漫画原著结局关键细节的改动”还是让这部电影毁誉参半。
虽然扎克施耐德对漫画原著抱以极高的敬意,并尽可能遵照原著完成了改编工作,但这仍然无法讨好早已心灰意冷的阿兰·摩尔。早在电影开拍之前,戴夫·吉布森告知摩尔《守望者》电影化的消息,摩尔表示不会阻拦,但要求自己的名字不要出现在电影当中,甚至愿意将自己的分红归于戴夫,他只希望自己能与DC彻底断绝关系。“没错,这书曾经让我引以为豪,可它现在带给我的只有谎言与欺骗……我连家里都没留一本。”——这是阿兰·摩尔对《守望者》最后的评价。《守望者》电影上映之后,摩尔拒绝观看电影,他的理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把这部漫画成功搬上荧幕。

虽然没有得到原著作者的肯定,但本片还是成为了导演扎克施耐德正式进入“超级英雄电影领域”的敲门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