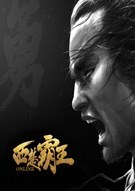游民讲武堂:中国古代,如何上演“万人攻城”?
在唐代,对攻城兵器的描述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个词——“人马俱碎”: 无论是早期与其他割据政权的较量中,还是后来对边境地区的经营,唐朝的攻城武器始终以威力巨大而闻名。比如说唐初李世民围攻洛阳时,抛石车所用的石块,重量约等于今天的30公斤;在李绩进攻高句丽期间,使用抛石机的射程已经达到了1里,相当于今天的531米。
这种变化,与唐朝所处的军事环境有关:首先,在隋朝及之前,中原地区的坚固城池就为数众多,而唐朝的统一,恰恰建立在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攻坚战之上;而在唐朝前期,其主要对手是周围少数民族政权,比如吐蕃、西域各国和高句丽——他们的生活方式早已从游牧转向了农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建造了大量夯土,甚至石制的坚固堡垒。

唐朝时期的要塞城市防御体系复原图,在城门等关键位置,其材料已经使用了城砖
毫不奇怪,唐朝攻城武器的数量、尺寸和威力都大幅提升,它们投入战争的数量也让人震惊。在乌鲁木齐的新疆博物馆,至今保存着当年侯君集征讨高昌的碑文,其中,对攻城战有这样的描写:
“伐木则山林殆尽,叱咤则山谷荡薄。冲梯錾整,百橹冰碎,机桧一发,千谷云飞。墨翟之拒无施,公输之妙讵比。”
“抛车石击其城中,其所当者无不靡碎……城中守卑者不复而立。”

高昌城旧址,由于战乱和气候变迁等原因,荒废于12世纪之后,640年,当地曾为侯君集率领的唐朝大军攻陷
这块碑文赞扬的,是唐太宗时期的左屯卫将军、行军副总管姜行本,这位技术官僚之前曾负责宫殿的修造,在讨伐高昌期间,负责带领工匠制造各种攻城设备。为攻克高昌,他建造攻城器械用了大约100天;为取得所需的木料,他甚至砍伐了整片森林。的确,在碑文中,对战争的描写有歌功颂德的成分,但无可否认,正是在这些武器的掩护下、唐军迅速席卷了高昌全境。

《姜行本纪功碑》原立于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县境内,现藏于乌鲁木齐新疆博物馆,该碑刻于640年,记录了左屯卫将军、行军副总管姜行本制造攻城器械,一举攻克高昌的事迹。公元645年,姜行本在随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期间,在进攻盖牟城的战斗中中流矢身亡,追封郕国公,陪葬昭陵
在进攻高昌期间,举足轻重的另一种装备,是大型的床弩,这种武器的历史同样能追溯到春秋战国,在东汉末年重新开始装备部队。最初,它们的作用仅限于摧毁敌军的木制塔楼和栅栏,但在唐初,其地位已经举足轻重,其优势在于可以随部队进行机动,并且威力不逊色于小型投石机。
史书记载,唐军装备的“十二石”强弩,需要用绞车张弦开弓,其弩臂上有七条发射弓箭的轨道,最中央的一条摆放一枝巨箭,“长三尺五寸”“粗五寸”,左右各放三枝略小的箭,当这七支箭共同射向敌城时,“所中城垒无不摧毁,楼橹亦颠坠”。另外,它还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当箭头插入城墙后,士兵可以借此进行攀登,因此又被称为“踏橛箭”。
为唐朝攻城武器发挥威力提供保证的,既有技术上的改进(比如说采用了固定规格的箭矢、石弹),但更多只因为它们的尺寸更大,操作者的数量更多。按照当时的记录,最大的投石车需要大约250人操作——这一方面是唐朝军队规模的写照,但一方面,更像是冷兵器发展到顶峰之后的无奈举措。
不仅如此,筑城技术的进步,更让这些改进相形见绌,在隋唐时期,城墙的一些地段已经采用了包砖结构,虽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烧制城砖的成本相当高昂,但经过加固,进攻者要想破城而入,必然要付出更大的损失。

《清明上河图》局部,可见当时的汴梁城城门已经采用了砖石结构,它们给攻城器械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此时,突破城防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增加攻城设备的数量,让攻城成为一场玉石俱焚的消耗战,而见证它达到顶点的一幕,终于在北宋末年爆发了。
照史料记载,北宋军队拥有大量攻城器械,比如尺寸惊人的弩车、需要数百人操纵的巨型投石机和坚固的云梯,但遗憾的是,将当时攻城战推到新高度的,却是他们的敌人——兴起于中国北方的金政权。
在1126年,大举南下的金军扫荡了宋朝的北方边境,投降的宋军超过20万以上,在虏获的战利品当中,除了大量人口和财物,就是宋军装备的攻城兵器。此外,考虑到宋军已经使用了火药,金军对这些武器进行了特别加固,最终,它们在汴梁城内制造了一场浩劫。
在当时的记录中,留下金军“一夜安砲(投石机)五千余座”的记录,这还不包括投入的强弩和云梯,城内,每天被直接击中毙命的士兵“不下二三十人”,对有着大量防御手段的守城方而言,这已然是很高的伤亡率。

宋军使用的“七梢砲”,在靖康之变中,金军曾大量使用这种武器围攻汴梁城
不仅如此,金军的组织效率也达到了让人震惊的地步。投入数量如此巨大的攻城武器,自然需要准备数量惊人的木材和石弹,而当时的环境并不利于金军进行准备。因为汴梁城周围一马平川,既无森林山泽,也无石料可采,因此金军专门派出部队,搜刮周围的墓碑和石磨,并且拆毁民房,当汴梁陷落时,堆积在城下的石块高度已经超过一丈——它们也从侧面印证了攻城战的物资消耗水平。
虽然汴梁的陷落与守军的强攻无关,但这次围城,却充当了一段屈辱的开始,通过屈辱得到的教训往往最刻骨铭心,面对金国的后续攻势,宋朝人很快掌握了各种应对手段。
其中的佼佼者是南宋初年、一位叫陈规的官员。历史书上说他稳重沉默,待人平和,慷慨好施——有着一个模范的文官形象,但他之所以青史留名,却在于对攻城和守城战术的改进。
尤其是1132年、金军对德安发动的 9次进攻,每次都动用了抛石车、云梯、井阑和冲车,最长的一次轰击竟持续14昼夜,然而凭借着过人的谋略,陈规却屡屡以少胜多,其撰写的《守城录》,至今仍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之一。
《守城录》在南宋时期被广泛刊印,充当了各地守城的标准教材,和过去相比,针对骑兵和大型工程器械的使用,其中倡导的守城战术已经发生了极大改变。
这种改变体现在城墙外围、护城河之后的地区,守军会在城墙6-9米外,铸造一道高 4米,厚 3米的羊马墙,羊马墙之后一道壕沟。之后又是一道墙,这样,就形成了两道壕、三道墙的复杂障碍系统,任何人想要逾越这些障碍,将至少暴露在箭雨下几十分钟。
同时,城墙顶缩窄至 5 - 6米,以降低被石弹击中的机会。此外,陈规还用能承受石弹轰击的平头墙取代有齿垛的女墙,并取消了搭建在墙顶部的木棚,城角也由直角改为半圆形,以减轻石弹的冲击力。
而防御战术方面,陈规更是抛弃了以往固守的观点,强调在城内保持足够的预备兵力,同时,他还提出了在城内部署投石车,尤其是用投石车摧毁敌人的攻城器具。
在《守城录》中这些提到:射程大约 500米的投石车,应当打击敌军将领营帐和抛石车阵地;射程 4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工兵的阵地;最后以射程 3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的攻城器械。同时,为了防止遭到反击,以及减轻运送石弹的困难,抛石车不设置在城头,而是隐藏在城墙内侧,由城头上的指挥员指挥射击。

反映1272年,蒙古大军围攻襄阳的艺术画,图中巨大的攻城机械是“回回炮”,即阿拉伯人使用的配重式投石机,据说,这种武器起源于怛罗斯之战结束后,由被俘的唐朝工匠为阿拉伯人制造,它在经过了诸多改进后,以一种讽刺的方式传回了国内
遗憾的是,由于南宋的软弱,陈规的思想几乎没有得到践行的机会,到南宋末年元军入侵时,仍然有大量的城市面对突袭毫无防备。不仅如此,对于那些抵抗的城市,除了面对蒙古人使用的配重式投石机——“回回炮”(阿拉伯人使用的配重式投石机,可以发射超过130公斤的石弹),还将面对另外一个威胁——火药,而颇为吊诡的是,没有人知道,蒙古人是何时,以怎样的方式掌握了火药的生产技术,但在对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战争中,他们却在火药的使用上表现出了惊人的效率——在此起彼伏的火光和爆炸中,冷兵器时代的攻与守正在退场,另一个时代的大幕已经徐徐拉起。
当然,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它们上演于备受争议的元、明、清三朝,而这个故事留给人们的,也许只有一半是骄傲,剩下的全部是屈辱和疑惑的回忆。
更多相关资讯请关注:西楚霸王Online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