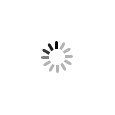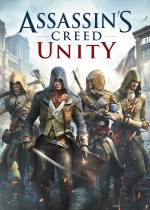刺客信条大革命 官方小说中文翻译
第4页:爱丽丝日记-1778年4月11日
展开1778年4月11日
I
午夜时分,我套上长袍,取了支蜡烛摸下了楼来到了藏书室等待威瑟洛尔先生。
他想办法进入了城堡,鬼魅一般地行动,那些狗完全没被打搅,他是如此安静地进入了藏书室而我根本没有听到门被打开及关上。他几阔步穿过空厅,从头上摘下了假发——那被诅咒的东西,他讨厌它——然后擎住了我的肩膀。
“他们说她恶化得很快,”他说,当然是耳语。
“的确。”我告诉他,低下了头。
他闭上眼,而虽然他并不已经苍老——才四十好几,略微年长于父亲和母亲——而岁月已经蚀刻上他的脸庞。
“威瑟洛尔先生和我曾经十分亲近。”母亲曾说过。她说出这番话时会微笑。而我设想她脸红了
II
我第一次见威瑟洛尔先生是在二月份异常寒冷的一天。那个冬天正是一系列酷寒冬季的第一波,但是在巴黎当塞纳河洪涌接而冻住时,那些困顿窘迫的人们在大街上垂死挣扎着,而在凡尔赛情况则是另一番景象。等到我们醒来时早已有人生好了在那些炉格里咆哮的火焰,然后我们会享用热气腾腾的早餐,暖洋洋地裹在绒毛里,在上下午我们四处闲逛时手上也会套上暖和的皮手套。
在那特别的一天艳阳高照,虽然这完全没褪下那彻骨的寒冷。一层薄冰在厚厚的雪地上漂亮地晶光闪闪,它是那么坚硬就连斯格莱奇(Scratch),我们的爱尔兰猎狼犬,也能在上头行走而利爪不至于陷进去。它会试探性地走几步,然后意识到这一好运而兴奋地吠着,接着在我和母亲艰难地试着到达南边草坪边缘的那棵树时它便径直向前冲去。
握着她的手,我一边走着一边从肩上瞥去。远远地我们的城堡在阳光和雪地的反射下熠熠生辉,它的窗户像眼睛一样闪烁眨巴着,然后,我们从阳光下走进了树丛,它便不再那么显眼,就像是被铅笔描摹地一般。我们比平常时要远得多,我发现,再也不在它的荫庇所能及了。
“不要惊慌如果你在树影里看到一位绅士,”母亲说,微微地向我弯下腰。她的声音很安静,我不由得将她的手抓得更紧,她笑了。”我们的在场的并不是巧合。“
那时我是六岁,完全不知道一位女士在那样的一个场合下与一个男人会面会别有“深意”。我所能知道的,仅是单纯地母亲与别人见面,并不比与她和伊曼纽尔(Emanuel),我们的园丁,的谈话有更多重要意义,或是和琴(Jean),我们的马夫,一起溜圈。
冰霜授予了这个世界沉寂。在树林里甚至比覆盖着雪的草地上还要安静,当我们从窄窄的小道上走向树林深处时不自觉地便被感染感到心神宁静。
“威瑟洛尔先生喜欢玩一个游戏,”母亲说,她的嗓音在这一片平和的荣光下逐渐缓和。“他也许会突然出现,一个人必须时刻注意等着他的任何意外。我们应该估计到周围的一切然后逐渐有根据地得出自己的预期。你有看见任何的踪迹吗?”
我们周边的雪地都完好如初。“没有,妈妈。”
“很好。这样我们便能确定附近的只有我们。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最可能躲在哪?”
“一棵树后?”
“好,很好——但是这里怎么样?”她暗示着头顶,于是我伸起我的脖子向上方树冠中的枝叶看去,冰霜在细碎的阳光的下闪烁着。
“观察任何一处地方,始终,”母亲微笑。“用你的眼睛去看,尽最大的可能不要去倾斜自己的头。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注意力在何处。在生活中你会遇到对手,而这些对手会从线索中尝试着去理解你进而清楚你的意图。让他们不断地去猜测来保持的你的优势。”
“我们的客人会在高高的树上吗,妈妈?”我问道。
她咯咯地笑了。“不。实际上,我早就看见他了。你看见他了吗,爱丽丝?”
我们停顿了一会,我看向面前的那棵树,“没有,妈妈。”
“现身吧,弗莱迪(Freddie),”母亲呼叫着,然后理所当然地,前方几码(一码=三英尺=0.9144米)的地方一名胡子深灰的男人从一棵树后走到我们面前,他从头上摘下三角帽又向我们行了一个十分夸张的鞠躬礼。
凡尔赛的人们有一种特定的方式。他们不管面对谁都会牢牢锁定住自己的鼻子。他们有着我所认为是的“凡尔赛式微笑”,吊在茫然和无趣之间,好像几乎就是在不断地传递着诙谐的打趣话,这就像是,所有在场的人都在接受审判一般。
这个男人并不是凡尔赛的一员;单单从他的胡子就能看出。而且尽管他正在微笑,那不是凡尔赛式的;取而代之,那是柔软同时又庄重的,是一张属于三思而后行而且言出必行的男人的脸。
“你蒙蔽了她的眼睛,弗莱迪,” 母亲说,正值他向前走来,亲吻了母亲伸去的手背,接着对我也做了同样的,再次躬下身来。
“真的吗?”他说,他的嗓音温暖又轰隆作响却毫不造作,一名水手或是士兵的声音。“噢,真该死,我一定失了自己的分寸。”
“我希望还没有,弗莱迪。”母亲笑了。“爱丽丝,来见过威瑟洛尔先生,一名英国人。同时也是我的一位伙伴。弗莱迪,这是爱丽丝。”
一位伙伴?像乌鸦们那样?不,他没有一点与他们相似。与其向我瞪眼,他牵起了我的手,躬下身并亲吻了它。“真令人着迷,小姐(mademoiseller,同英文miss)。”他用略刺耳的声音说。 他的英国腔碾压着这个词“小姐(mademoiseller)”让我无法制止地觉得魅力十足。
母亲以一脸认真的表情正色道。“威瑟洛尔先生是我们的心腹朋友和保护者,爱丽丝。一个你可以随时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去找的人。”
我看着她,感觉有些张惶,“那父亲呢?”
“父亲深深地爱着我们两人,而且十分乐意将生命献给我们,但是像你父亲那样居于要位的男人,需要蔽于家内事责的干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威瑟洛尔先生,爱丽丝——你的父亲不应该被女人所要操心的事所打扰。”她的眼神甚至更加尖利。“你的父亲一定不能被打扰,爱丽丝,你清楚了没有?”
“是,妈妈。”
威瑟洛尔先生点了点头。“我随时在这为你服务,小姐,”他对我说。
我屈膝行礼。“谢谢你,先生。”
斯格莱奇也到来了,兴奋地问候着威瑟洛尔先生,他们俩很明显已经是老朋友了。
“我们能走走吗,朱莉?”保护者问道,他戴上他的三角帽,并向我暗示他们俩要一同走。
我保持在他们身后几步距离,隐约听到些他们低声谈话的短暂片段和不连贯的部分。我听到了“大师”和“国王”,但这只是几个词,我早就习惯的在城堡里门外听见的那一种。在我发现它们所承载的重大意义时这已经是老久以前了。
然后那件事发生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已经记不清事件的顺序。我只记得看见母亲和威瑟洛尔先生在斯格莱奇突然毛发竖起并开始低吼时全都陷入了紧张的气氛。接着母亲迅速转身。我的目光随着她注视的方向而去,并在那看见了它:一只狼矗立在我左方的矮树丛里,一只黑灰相间的狼绝对静止地立在那些树的中间,以十分饥饿的眼神打量着我。
有什么东西从母亲的皮手笼里闪现。一支银制利刃,两快步的功夫她便穿到了我身边,将我揽到她的身后,于是她能在我攥住她的裙角时面对那只狼,伸出她的剑。
在小路的另一边威瑟洛尔先生抓住了准备全力应敌、毛发竖起的斯格莱奇的后颈,而我注意到了他的另一只手伸到了悬在他一侧的剑把。
“等等,”母亲令道。一直手升起挡住了威瑟洛尔先生前方的道路。“我不认为这只狼会攻击我们。”
“我没有那么确定,朱莉,”威瑟洛尔先生警告道。“你傍上的那是一只看上去格外饥饿贪婪的狼。”
那只狼盯着我的母亲。而她同时看向正后方,与我们交谈。“这山丘上没有什么能供它吃的了;是窘迫将它逼上了我们的土地。但我认为这只狼明白如果它攻击我们,它将成为我们的敌人。对它来说在面对无法取缔的力量和他处潜在的食物时撤退会是个再好不过的选择。”
威瑟洛尔先生短短地一笑。“为什么我闻到了寓言故事的难闻气味?”
“因为,弗莱迪,”母亲笑道,“真的有这样一个寓言。”
那只狼继续集中着目光,一点也没有从母亲身上移开,直到最后它垂下了它的头,转身并慢慢小跑了远去。我们看着它在树丛中消失,母亲也收起了剑,站定下来。
我看向威瑟洛尔先生。他的夹克再次被扣上,完全看不出那柄剑的存在。
而且我离那枚掉落的便士又再近了一步。
III
我将威瑟洛尔先生领到了母亲的房间,他要求与她单独见面,并向我保证他能独立离开这里。很好奇,于是我从匙孔中窥视过去,看见了他坐在了她的一旁,牵起她的手并弯下他的头。不一会我便听到了他的抽泣声。
更多相关内容请关注:刺客信条:大革命专区
责任编辑:Shy夏夏
- 第1页:亚诺日记-1794年9月12日
- 第2页:爱丽丝日记-1778年4月9日
- 第3页:爱丽丝日记-1778年4月10日
- 第4页:爱丽丝日记-1778年4月11日
- 第5页:爱丽丝日记-1778年4月12日
- 《超级忍 反攻的斩击》官方中文版下载
- 《合金装备3:重制版》官方中文版下载
- 《回音点新星》官方中文版下载
- 《可口的披萨,美味的披萨》官方中文版下载
- 《Nexus Defenders》官方正版下载
- 《法国小馆儿模拟器》官方中文版下载
- 《Tile Cities 2》官方正版下载
- 《Coloring Game 10K》官方中文版下载
-
 喜欢制服play的有福了?油光满腿的翘臀囧图
喜欢制服play的有福了?油光满腿的翘臀囧图
 《异度之刃2》高清复刻版或已曝光!开发商暗示
《异度之刃2》高清复刻版或已曝光!开发商暗示
-
 《FZ地平线6》再获证实 爆料人可能是为报复微软裁员
《FZ地平线6》再获证实 爆料人可能是为报复微软裁员
 30岁玩家遭健康预警:熬夜久坐不运动 爱吃垃圾食品
30岁玩家遭健康预警:熬夜久坐不运动 爱吃垃圾食品
-
 UE5不背锅!开发者称游戏优化糟糕问题在于开发者
UE5不背锅!开发者称游戏优化糟糕问题在于开发者
 拼多多楼下彩票店开出778万元大奖 极可能是员工中奖
拼多多楼下彩票店开出778万元大奖 极可能是员工中奖
- 老男人的手还能跟上新时代的思必得吗?
- 性取向不合但性张力拉满 寡姐和gay蜜乔贝贝新照曝光
- 张靓颖自曝健康问题:一伸懒腰手掌就流血
- 票房扑街!吴京参演《再见 坏蛋》上映5天票房仅25万
- 艾玛·沃特森新照曝光!开心徒步走出表情包
- 腾讯《怪物猎人》新作首次公开试玩来咯!参展TGS
- 曝《地平线6》将于9月TGS公布:在日本飙车竞速
- 曝《GTA6》重金开发水体物理效果!首次加入冲浪
- 《异度之刃2》高清复刻版或已曝光!开发商暗示
- 雷军发来贺电:奔驰太强了有点变态!